“我特殊的母语”
是“土著人的话”,或的确是一种完全特殊的语言?畅销书作家Wladimir Kaminer在母语日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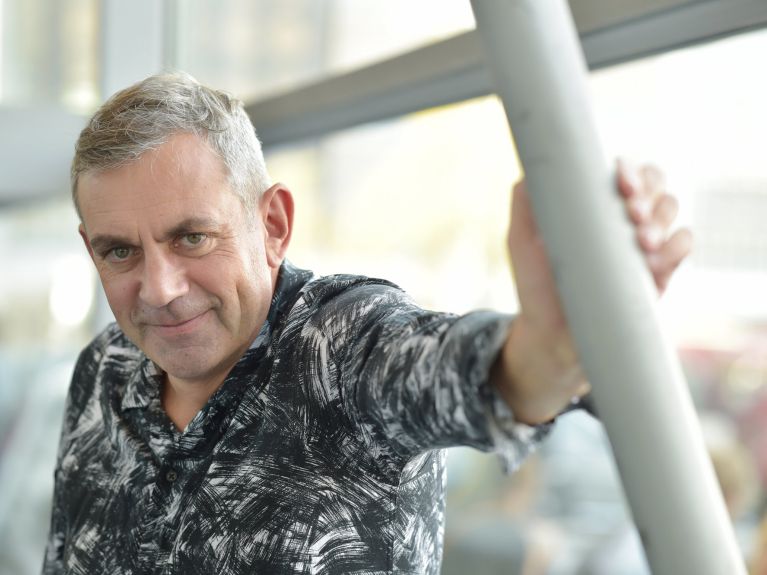
20年前,长篇小说《俄罗斯迪斯科》(Russendisko)令在莫斯科长大的作家Wladimir Kaminer国际知名。现年52岁的Kaminer自1990年起生活在柏林,用德语写作 – 而非他的母语俄语。一篇“母语日”特邀稿。
“您不用母语写作?这对您来说一定非常难!”—我总是听到这样的说法。其实我最近刚刚开发出一种母语。我母亲今年89岁,听力不好,却不愿戴助听器。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会变得对噪音非常敏感。我母亲说,戴着助听器她无法吃早餐或看电视,因为她会听到自己咀嚼或猫咪打呼噜的声音,而周围人说话的声音却仍然太轻,听不清,遇到高声调的人说话时尤其如此。
Dieses YouTube-Video kann in einem neuen Tab abgespielt werden
YouTube öffnen因此我开发出一种特殊的母语来与妈妈交谈,我尝试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与她说话,同时打手势,每句话重复两遍。这很管用。可能这种交流方式也对我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我虽然用德语写作,但我也尝试像和妈妈说话时那样用清晰、易懂的方式表达。在俄语中,“语言”是一个阳性词,与母亲无关。如果直译成德语,俄语中的母语被称为“土著人的话”。
我的孩子出生在德国,并在双语环境中长大,他们很顽皮地声称自己根本没有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母语,他们的母语是一种几乎没人能懂的密语。他们的语言空间就像一套两室户公寓。在家里,他们从父母这里听到的是充满了粗话词汇的俄语,因为在俄语中,许多有关复杂人际关系的内容只有用特殊的粗话才能描述。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成功地学会了萨克森话。出于历史原因,在东柏林的幼儿园中,大多数保育员来自萨克森,因此所有幼儿园的孩子都学会了这种美妙的方言。它让我想起鸟儿的鸣叫,想起那些有些茫然的鸣鸟,它们不知道该迁往南方还是留在东部。
如今,孩子们说,当他们与同龄人一起回忆幼儿园时光时,感到很困惑。虽然大家当时都唱同样的歌,但他们可能对那些歌有错误的理解。“小女巫碧碧”(Bibi Blocksberg)也是一样。直到很久以后我女儿才意识到,这部影片中不是只有碧碧是女巫,而是所有女孩子都是女巫。
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是德国人,德国人认为他们是俄罗斯人,只有他们的母亲真正理解他们,因为她能听懂那种神秘的母语。
抽奖活动
值“国际母语日”之际,Deutschland.de正在组织抽奖活动。2020年2月17日至28日,你可以在这里报名并有机会赢得一台灵巧的数字翻译器和吸引人的德语学习包!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regular information about Germany? Subscribe here:


